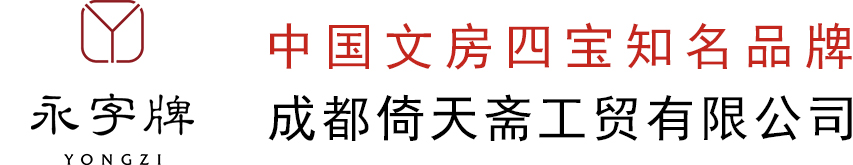
取消
清空記錄
歷史記錄
清空記錄
歷史記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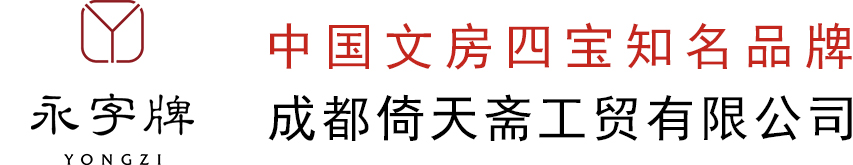
篆刻心得十二則
1立志與排難
我們想做一名篆刻家,有這個志向,這是很好的事情,但要成為篆刻家很難,難在哪里?就我自身的體會來講,我年輕的那個時代,也沒什么專業篆刻家,有的是一些刻字店、刻字廠,這是兩碼事。所以當時要立志搞篆刻藝術,有工作之累、有身體之累、還有長輩和妻兒之累……有心而無力,總覺得條件不具備,一大堆的事情壓在身上,總覺得條件不具備,不是你想搞就搞得起來的,這就成為有些人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乃至放棄的原因。
不知大家有否同感?我年輕時感觸就很大,所以我說立志當篆刻家、書法家,首先要解決“排難”的問題。比如我當時在部隊,別人有時間就下棋、打球….而我就是一有時間就寫字、刻印。有時還有很多壓力,比如你到地方上去請教一些著名的老師,當時領導就會講現在階級斗爭復雜,他們都是些舊社會來的遺老遺少,要警惕,少接觸,而且你玩的是封建沒落的東西。
所以一個有志搞藝術的人,光有立志決心還不夠,還要排難。我現在接觸一些老朋友,常與我講現在不搞藝術了,我問為什么?回答說有這樣或那樣的困難,我感覺很現實。
搞藝術的人,不是等好條件送上門,而是時刻珍惜當下,努力創造條件,排除困難去搞藝術。如果一定要等到自己條件好了再搞,那么我想,這一輩子可能都不會有理想的條件等著你。
我年輕時,一家五口三代人,就在10個平方的斗室里住了十四年,那房間被一隔二,我老母親和兒子睡在床上,屋里活動空間很難。我和我愛人睡在外面,沒有床,她和女兒睡在地板上,我就睡在方臺子的下面,就這點地方,頭就枕在門要打開的地方,晚上如果有朋友來,我得叫他等5分鐘,把鋪蓋卷起來,然后才能把門打開,朋友脫鞋子進來,晚上朋友走了,把地拖干凈、等乾透才能繼續睡,這個條件是極差的。要寫四尺的字,要畫四尺的畫,沒有這個空間,怎么辦?把一個小方臺的兩端添加兩個活絡的木板,平時是放下來的,要用時,就把板撐起來,畫畫寫字。有時就趴在地上寫字畫畫。所以我年輕時,寫字、畫畫、刻章、寫文章一樣不拉,不是我本事大,而是力爭擠出時間、擠出空間來,多做一點事情、多學一點東西。星期天我把愛人和孩子送到丈母娘家里,這10平方就是我的天下,晚上等他們回來了,我只有門后那一點空間放個小木凳,刻印聲音使他們睡不著,寫字畫畫但桌上又堆滿白天放在地上的東西,沒辦法,所以晚上我就寫文章,如此困苦的條件我都克服過來了。所以我說在座的年輕朋友,你們今天的條件肯定要好得多,無論是書房條件、生活條件、讀書條件…..我們那個時候需要的藝術書非常缺乏,不像現在走到哪里都能買到看到需要的書。
我們搞藝術的朋友首先要解決“立志”和“排難”的問題,你講你沒條件,我講條件都是自己創造的,絕不會萬事俱全,只等著你去揮毫走刀。你們可能覺得這個話題多余,其實人生有九九八十一難,不時都會有諸多的困難冒出來,所以我們立了這個志向,就要堅定不移的排除萬難走下去。堅持走下去,一定有成績。
2寂寞與燦爛
很多人覺得搞藝術的人很光鮮,有名有利。就我個人心得來講,搞藝術的人首先是要耐得住寂寞,有很多同學來我這,我講跟著我學習可以的,學費我也不收的,但有一點,必須耐得住寂寞,至少5年,不算多吧?
你今天拿篆刻刀,明天就想成為篆刻家,后天就想入西泠印社,再后天就成為大師,天下沒有這樣的稱心事。寂寞很重要,要甘于寂寞、耐得住寂寞,冷板凳要坐10年,其實搞藝術要出大成績10年遠遠不夠,也許還只是個零頭。
我從小就喜歡藝術,回憶自己參加西泠印社的展覽會是23歲,那就是我學刻印的17年以后。我參加書法展也是1963年,是我學寫字的19年以后。這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,而這也只能稱是真正的起步呢。要真正沉下心,沒有真正的寂寞,對藝術的敬畏和虔誠就沒有真正的藝術。
藝術絕不是炒作出來的,不是吹捧出來的,因為沒有經過面壁苦修的寂寞,沒有經過嘔心瀝血的洗煉,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。
搞藝術的人要有平常心,要耐得住寂寞,在此前一定要沉下去、再沉下去,把名利拋在一邊,沉到底,當然藝術其實是沒有底的,海有底。當寂寞走到盡頭時,往往就是燦爛呈現之時。
比如我年輕時發現印學方面的書很少,原鈴印譜也都更不易得。所以我從十幾歲開始,看到好印譜就做筆記。到上海博物館、圖書館、外地圖書館及私人藏家處去讀印譜及印學著作,乃至到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,看見好的材料就記錄在冊。
這期間就有很多趣事,我到天津圖書館借書看,工作人員問我想借什么書,我講我叫不出書名字。那人很奇怪,借書卻叫不出名字,以為我跟她開玩笑,我講我叫得出名字的印譜類書都看過,我就是想要看古人講的“要讀未見之書”。于是圖書管理員把我帶進去,我看了內部的書目卡片,果然有兩本沒見過的書,一本是李叔同早年的印譜,一本是被乾隆焚毀的周亮工編的《印人傳》,其實叫《印人傳》是不準確的,其真正全稱是《賴古堂別集印人傳》。乾隆時這書已毀,嘉慶以后翻刻本亦丟三拉四,多訛誤,不完整,全貌盡失。諸如,我曾讀到一本《宣和印存》,經考證之后發現,有《宣和畫譜》、《宣和書譜》,但世上并無《宣和印譜》,顯然那本《宣和印存》是明末人偽托的,據此《辭海》原有的這個條目就給刪去了。
在這幾十年當中,我前后讀過四千種印譜及印學論著,并不是我要標榜什么,只是說明要耐得住寂寞,要下苦功夫,盡可能多地讀書,掌握一手材料,那么你判斷思考問題就會有扎實的基礎。
我的《中國印學年表》,撰寫用了近50年,2014年是第3版,從1987年第1版到1994年第2版,跨度也有十幾年時間,如果不是耐得住寂寞行嗎?我花了15年時間編著《中國篆刻大辭典》,現在網上炒到九百多元一本,這本辭典目前我還在修訂,爭取明、后年再出第2版。
所謂“耐得住寂寞”,不是整天在那里歇著或空想,而是做學問要沉下去要做扎實,學習、實踐、思考、再實踐。所以不是面壁10年20年,哪有什么成就?栽樹開花結果是要等待的,果農都知道桃三、李四、杏五。“梅花香自苦寒來”這話都早已講爛了。
我喜歡畫荷花,一到夏天所有花都蔫了,唯有荷花在陽光越強烈處開得越好,古人總講“亭亭玉立”、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卻總不論及它的迎酷暑而傲放,我講荷花有其剛毅的性格,梅花不怕冷,荷花不怕熱,所以若不能吃苦、若不能耐得住寂寞,是不會有成果的。
3卡殼與闖關
我從小寫字刻印遇到的卡殼很多,就是再聰明的人、有再好的老師,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。藝術之路是顛沛坎坷的,就像爬群山,爬上一個山坡,然后就向下走了,再爬上一個山坡,然后又向下走了……,是趨勢向上的“M”型行進。
我15歲到30歲之間,是卡殼最嚴重、最苦惱的15年,學藝的成績時好時壞,有時甚至懷疑自己不是這塊料,不知在座的同學們有否這種情況?我那時喜歡看哲學書,有時看自己的印刻得比數月前刻的還差。可是我善于自我排解,認識是從實踐中來,眼高手低是符合規律的。
那為何會刻的印寫的字反而不如以前呢?要么就是你不努力,但若是在不斷學習前進的過程出問題,那就是“眼高手低”在起作用,即眼光提高了手還沒及時跟上,就會出現卡殼、苦惱,這恰恰是證明自己正處于大踏步前進的前奏,是好消息。所以遇到卡殼現象千萬不要灰心氣餒,因為你在攀登新坡、你在曲折中前進,知難行難,你就會克服這個困難。
那時我在犯這類“今不如昨”的苦惱時,我會以平常的心態去體悟名家印譜,以解決刀法、章法問題。去讀些大文化方面的詩文,過段時間又會覺得水平又上去了,所以經過這段時間,就是我爬坡最累、最苦、最易產生動搖的時候。藝術之路絕不是一帆風順的,上上下下、進進退退是正常的,你要準備好吃苦到底、堅持到底的堅韌不拔的精神,它一定會確保你可以柳暗花明,在迂回中繼續前進。
4印里與印外
畫畫有寫生,書法篆刻沒法寫生的。祖先給我們創造這門藝術,入門除了臨摹學習,幾乎再無第二條途徑。有些大藝術家,也是在有相當深厚的積累和感悟之后才有“屋漏痕”、“折釵股”、“萬物皆入書、入印”的超跨度的變通能力,初學者只能“印內求印”,印宗秦漢、隋、唐、明清流派印,在嬰兒期不吃這口奶是不行的。
浙派創始人丁敬就說,周、秦、兩漢、魏晉、隋、唐、元、明、清每一個時代都有特色,把印里的營養都吃遍了。鄧石如開始了“印外求印”的觀念,以篆書入印,他的印是有起、落筆的,其印不全是從印里來,是從碑刻里來的。
趙之謙的聰明在于,他所處的時代出土了很多前人未見的既古而又新的文字,他是非常敏銳而且擅化的人,善于將新出土材料直接用入刻印,所以五百多年的明清篆刻史,像趙之謙這樣的百變金剛就這么一個。
一個真正的大篆刻家,絕對是有自己的一套獨創的新理念,不見著述、不講出來不代表他沒有,這是我們研究篆刻史的人必須要敏銳感覺并注意的。
之后的吳昌碩,從出土的封泥之中體會到了一些瓦甓之美,斑駁之妙封泥印不是平面的,而是有起伏的,富有輕重節奏感。線條亦不是光溜平滑的。而是有浮雕般的質感,吳昌碩感悟到這點,他高明的做印技巧是前無古人的。古人也做印,是將刻好的印放在一個小盒子里面,吩咐書童搖,以此達到做舊目的。而吳昌碩是理性的,帶有很高的藝術內涵去做印,其印鈴蓋出來的印面效果,在平面紙具有浮雕般的質感。
搞篆刻的人,首先要在印里好好學習,日后再要到印外去好好參悟,這印里和印外是一個辯證關系。路不是已經被前人走完了,而是要靠你自己去發現。
我年輕時是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,19歲那年當海軍到溫州,從船夫搖櫓過程中發現自在入水淺,遂得篆刻中深入不如淺刻。此外,真正優質的長線條是由若干曲線組成的,比如用圓規畫出的圓,那是缺乏趣味的。這與我們書法里的提按起伏同理,好的篆刻家要有很強的變通能力,要努力去發揮藝術的想象力。
刻印中有疏密的關系,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喜歡看古巴女排和中國女排比賽,男排只講扣殺沒有看頭,女排比賽兩強相遇,根據球路,則有站位換位和大密大疏、且出人意外節奏的變化,這不僅是看球,而是去關注全場瞬間千變的章法布局,我以為對刻印的布局就大有裨益。
古人的“計白當黑”、“積點成線”,雖然這些話經典,但我們更應該從生活當中去真正感悟活生生的、有滋有味的章法布局和線條揮運。比如以前我們部隊拔河,繩子放在地上并不見力量,但拔河時,兩隊都拉著這繩子,此時繩子一會朝左、一會朝右,這富有張力和阻力,這有生命活力的繩子就等同于篆刻里最優質的線條。
所以搞印章的人更應該從潛移默化的生活中去感悟、去發現,在具有一定基礎之后,這些就演化成為藝術中非常重要自我而獨到的東西。
5秀美與雄遒
篆刻風格大致分為兩類,寫意與精工。從印風上講,是沒有好壞高低之分的,但值得注意的是,風格是會因時而沉浮,然而內在美是千古不變的,如此理解是科學而公平的。
在座的印友們,據我所知就有刻各種風格,百花齊放都是可以的。但不能因為你的喜好去否定蔑視別的風格,這不好,要不同而和,要客觀。
我想告訴大家,具有一定基礎之后,不要急于給自己定型,因為我們年輕,有的是時間,要繼續拓寬視野,什么東西都要去嘗試,接不接觸新東西,其感覺是不一樣的。我就經常對學生們講要多嘗試,不去嘗試其間的美和特質你就體會不到,自我封閉切切不可。
記得1974年周昌谷先生囑我刻過一批印,他請朱關田先生拿去給沙老看,之后沙老給昌谷寫了一封信,高度地表揚了我,我很感激。1975年我隨朱關田先生去拜見沙老,我帶了本二十七八歲變法后的印譜,請沙老指點,沙老問我是不是想定型,我講在探索并不想定型。我去年出版了兩本印譜,都是不同時期的,可以看出至今我還一直在變。搞藝術的人是不能定型而一成不變的,不變就會僵化,講變化也要有一個主調,可以有一個主調,總之,常變才能常新。
此外,我還要談一個現代印風的問題,我從來不反對探索,對現在千奇百怪的風格我從來不反感、不反對,歷史上任何一個新風格出來時用老眼光看都是奇怪的,但反過來講,奇怪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新的東西,不一定是能站得住的東西。新奇的、有內涵的才能成為經典,不去探索就不會有新東西,我們不應對“現代印風”翻白眼,橫加指責。我只是認為叫“現代印風”,這是不科學的,你叫現代的,那其他的品類就是古代的么?我主張應該用“實驗”來命名,不妨稱之為“實驗印風”,實驗有可能成功,也有可能失敗,所以用實驗來說是科學的,我們不要過早的去抨擊打壓,或是鼓掌贊揚,時間才是檢驗它是否成功的最公正、最科學的試金石。
現在我們書法篆刻界有一種丑書、丑印。此處所說“丑”不是“差”,與“丑”對立的不是“美”,而是“媚”。因為從真正的美學角度講,“丑”無可指責,是站得住腳的。“丑”的對立面是“媚”,而不是“美”,這是不能混淆的兩個概念。“丑”里面也是有高低好壞優劣之分的,真正有內涵的、百看不厭的“丑”,其本質真諦也是“美”。
舉個例子,京戲三國演義空城計里的蔣干,是一個丑角,名丑蕭長華演得妙趣橫生、入木三分,大家都對他贊不絕口,丑到極點,神采飛揚銘刻不忘,就是美。所以我們在談風格的時,把這個問題也說一下。
6刀石與筆墨
這個問題很具現實意義,趙之謙說過“古人有筆又有墨,今人唯有刀與石”,他把刀石與筆墨對立起來議論,這就缺少一點辯證法,只講筆墨沒有刀石能是好作品嗎?其實他自己的作品倒是都有兼顧,兩者不能對立,要相輔相成,合則雙美,離則兩傷。
簡而言之,刀石是技法,筆墨是書法。趙之謙是一位天才人物,但也不免“尺有所短”。他說錢松刻印淺,他的深,成效確是一樣的,其實是不一樣的。趙之謙缺少錢松印之醇厚,原因就在于他刻得深,趙是推刀法,錢松善于用沖、剔、切三種刀法相結合,用刀技巧不同,刻出來印面效果也大不同,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刀法是門獨立的學問,不能不去作深入仔細的研究與實踐。今天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,我們所見到的優質原鈴印譜太少,我們所見多是印刷本,且是翻版多次的印刷本,這就是我們往往不能深入的原因。印鈴出來的線條厚薄與用刀的高下息息相關,建議大家多看看名家刻原印石,一定可以獲益良多。
7傳統與創新
傳統要不要?這是個問題經過十多年的研討,已經解決了,我們現在所說的傳統,都是經過淘汰留下來的優秀傳統,這些優秀傳統并不是要不要的問題,而是必須去認真學習的。
我觀察現在的印壇,有三種情況:第一種是學優秀傳統,非常忠實的表現優秀傳統,這沒有什么不好的,喜歡這一路,一輩子就這么搞,如果能夠作優質傳承,也應該贊賞。第二種是認為傳統是種束縛,不需要學,就要玩自己的,這也沒什么意見,藝術本來就是玩,少營養,缺基因,玩得也可不亦樂乎,痛快、自由,但能取得大的成績很難。第三種就是認真學習傳統,但又思考怎么突破傳統,這個我很贊賞。我們篆刻藝術的發展與突破就在這第三種人群中,他們真正具有推陳出新的時代責任感,我尤其贊賞。
但還有一部分人有誤區,說傳統沒什么好學的,我在幾十年前寫文章曾講“傳統萬歲,創新是傳統加一歲”,講傳統與創新的辯證關系,千萬不要進入誤區。學習傳統同時要心想著推陳出新。
近些年我又做了些哲學思考,“推陳出新”的本諦應是“推新出新”,無論時間過去多久,那幾個開創新派的大師,他們仍是光芒萬丈,永遠是新的!你一味地模擬他們,你才是舊的。所以我們學習傳統,是在學新而不是學舊。這些大師的作品理念,包括他們開創的新面對我們而言永遠是新的,向他們虔誠地學習是學新不是襲陳,所以本質是“推新出新”,我們要非常辯證的看待以往優秀的傳統。
我們往往有一個誤解,新的對立面是陳的,陳意味著是我們前進的障礙絆腳石,其實陳的藝術是有精華與糟粕之分,有出新的與陳腐之分,能智慧而明確地去學飽含精華的往昔之新,是“推新出新”。所以中國傳統藝術一定是串聯的長鏈,是有傳統再有其后出來的創新,像鏈子般一環扣一環,緊緊相扣的。
我1986年到新加坡開畫展、講學,那時正是處于“中國畫走向窮途末路”的大討論,新加坡同道們問我到底該不該新?那會兒中國改革開放剛起步,新加坡確實是一個花園城市很新,我問你們新加坡夠新了吧,還要再新嗎?他回答當然要!什么東西不需要再創新呀?
我還舉了個例子,我生下來七斤半,這個就是我父母給我的“傳統”啊,我四十多歲了,體重增加到一百六十斤,這也就是出新啊。你想如果要一味割掉傳統,你覺得我該割掉身上哪七斤半的呢?這不是割肉,而是割命!
所以傳統和創新是不能割裂的,那些割裂傳統的東西是必定不能扣到這條鏈子上的,“推陳出新,百花齊放”這是藝術亙古不變的規律。
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出新的方向,現在有個論調叫“放開膽子來,前人沒弄過的我來弄”,這個我贊成,但只有怪異的才是創新這見解太偏頗、太極端,那雅致、秀美、雄渾的那類就沒法再創新了嗎?創新之路有千萬條,寬廣之極。創新是一個非常高的標準,這與新鮮是兩碼事,我們“9·3”大閱兵,一個個方隊走過去,整齊劃一,如果大家都穿海軍服,突然出現一個陸軍服裝,大家都會朝他看,這叫新鮮出跳,不叫創新。要創造一個有分量的大家公認而信服的創新,是很難的。丁敬身的時代距今已有三百年了,鄧石如、吳讓之、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齊白石等,三百年才出來幾個篆刻大家呀?可見是難于登青天的。
我還有幾個問題要說一下,我們現在學習傳統,主要是看印譜,我可以很負責的告訴大家,這些出版社都是很有名的,編者也是很用心花了大力氣編成的,可是我一本也沒有買,就是它印出來的印章,不能作為我們學習觀摩、臨刻的資料。這不能怪編者,因為他們手上沒有這么多原打印譜,書和文章寫好了,再從別的印譜中選取圖片,反復翻版的印了,還剩多少原印的本來面目?往往會誤人子弟的。
前幾年我和幾位同學寫過一本《篆刻三百品》,我當時講過一句大話,咱們這本書就算文字寫的不好,但配圖你們絕對可以作為學印、臨刻的范本,因為我都是用原打印譜,照相制版印刷的,不是翻版的,這與其他印譜書比較你會發現有很大區別。
古印人中,我認為用刀最好的是吳讓之和錢松,我手里有一些他們的原作,他們不僅用角,還用刃、及刀背,所謂“寫字八面用鋒”,篆刻也要講究“三面用刀”,刻出來的印線才具有非同尋常的藝術性。
8刻苦與天賦
搞藝術你想真正進去,始終離不開刻苦兩個字。有些人認為自己有天賦,別人可能也吹捧你,可是搞藝術的人得刻苦。首先講,一年復一年的刻苦,天賦是在你刻苦實踐之后才能檢驗你是否真正有天賦,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天賦上。即使有天賦的人,都是不會預支的,笨鳥先飛,聰明的鳥更要懂得先飛!
古人講“吃得苦中苦,方得人上人”,但吃了苦也不一定成人上人,機遇和天賦也很重要。我年輕時李可染先生很看得起我,時時關愛我,當時我年輕狂傲氣,李老先生誠懇地告誡我說“天才不可仗恃”,一句話指引了我的后半生,讓我燥狷的心就沉下來了,循著老老實實苦行僧般的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。
9技法與文化
刻印作為一門藝術是有技巧的,僅膽大不是藝術,藝術者“藝”是技巧,“術”是學術,是文化底蘊,二字是可分開解,刻印時章法、刀法是技巧,但表現的是風神,這與你的文化底蘊有關,說到底還是要體現你自己的文化涵養。
技巧是骨肉、文化是靈魂。沒有靈魂的骨肉,只是行尸走肉,所以寫字刻印都要有文化來支撐。看作品的好壞,要從技巧和文化兩方面來分析。搞篆刻的各位,不要每天只知道捉刀刻石,要抓緊時間讀書,讀書是攻藝有成的第一要務!
拿我自己來說,我總結出四個字“詩心文膽”,意思就是從《詩經》到唐詩的精粹,此謂“詩心”;從司馬遷的《史記》到唐宋八大家的美文,此謂“文膽”。但是光有“詩心文膽”,沒有技巧也是不行的,比如聞一多先生也會刻印,他的詩文我讀過一些,寫得很好,評價也很高。瞿秋白寫的文章也好,也多,他也會刻印,他們的學問我很佩服,但印章真刻得不夠好,因為技巧不夠啊。所以一定要擺正技巧與文化的關系,有技巧沒文化,一定是沒有深度索然無味的,有文化沒技巧,也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篆刻家。
10表揚與批評
我們搞藝術的人一輩子都會生活在表揚、批評之中。但搞藝術的人必須要有胸襟,接納這一切。就算別人批評你,你也要接受,促使自己回去思考改進。表揚是糖,偶爾吃吃可以的,但批評更重要,表揚的是你已有的東西,批評是你還沒達到的且是必須要獲得的東西,所以批評更重要。
舉個例子,我15歲時候,拿了作品去給上海一很有名的書畫家看,結果被批評的很慘,甚至說“看你的字就曉得你活不長”的,當時受不了啊!我還是孩子,平時又被表揚多,后來想想,老人與我無冤無仇也是為我好。過了半年時間我又拿作品給他看,他前事盡忘,還表揚我說寫得好,還叫我刻了幾方印。這讓我從小就體會到「批評真好」。
還有一件事是,當時1984年,要我當畫院領導,我不肯干,領導發火,最后沒辦法,我只好干了。但同時我提出兩個條件:一是只管藝術不管行政,不要安排我簽字之類的雜務。二是我上半天班,還有半天我要研究我自己的東西,到了六十歲我堅決退休。在從政和從藝的問題上,我一直比較清醒,藝術比名利、比做官更重要,是終身的事業。
也是1984年,有一次請外賓吃飯時,一位畫家當著眾人面講我畫畫不行,我想想是對,以往是確實把精力都放在寫字刻印了。之后1985、1986、1987三年我就把重心都放在畫上,那段時間有人批評我印刻得沒以前好,這也沒錯。現在我的畫也已被人認可了,但當時畫被人抨擊時,我得承認心里也是不好受的,但人家的批評不無道理,當時是畫得差,“聞過則喜”我做不到,但聞過則改,改而進之,則就得感激批評我的人了。我很感激批評我的人,就是他才促使我努力去畫好畫的,所以不要不想聽別人的批評,這不是壞事。我對這方面心態還可以,我一輩子活在別人的批評、誹謗、嫉妒中,別人潑我的水我當汽油動力,別人批評得對你要聽、要接受。即使打錯了靶子,也不必上心。批評是對攻藝者胸襟的鍛打,有大胸襟才能出好成績。
我今年76歲了,最近發現一個問題,就是我的老師們都已去世,很少有人批評我了,都是文章鼓吹表揚的多,同學中也有很多有成績的,但我畢竟是老師,他們不好意思批評我,所以我現在靠的是自我糾錯、力求進步、自我批評,所以刻了一方印“三省吾身”。
最近我發現自己的膽子不如以前了,年紀大了刻多了,反而刻得小心了,所以我刻了一方印叫“放膽”,刻壞了怕什么,所以人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,自我批評,這樣才會有進步。
11專一與旁通
在座的都是以刻印為主的,有人講我又是寫字、畫畫、刻印還寫文章、還出書,有人開玩笑說“飯都被你吃光了”。其實掌握多門藝術的前提是我花了十年、二十年的時間深入進去刻印,把握了一定規律然后再去學校其他。書法和篆刻密不可分,我不建議用鋼筆、鉛筆寫稿子,我建議用毛筆寫印稿,這對書法刻印都有好處。
篆刻搞好了,可以再去寫寫字畫些畫,這些藝術其實都是近親,是一個馬蜂窩里靠在一起的蜂穴,你如果一門精通了,再去打通另一門往往可以事半功倍,觸類旁通,是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化學復合作用的,一加一,加一,加一,加一,一定至少大于五。所以首先要提倡專一,然后再旁通,一樣樣扎扎實實地打通,然后達到融會貫通,這方面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齊白石都是典范。
“一專”與“多能”不矛盾,可相輔相成,但需要長時間的循序漸進與歷練,以殉道者的平常心,甘于淡泊,耐得住寂寞地刻苦學習。倘使真正地把書畫印的蜂穴打通了,印章刻得好,深諳“計白當黑”,寫字畫畫的章法就不是問題;書法寫得好,筆劃圓健,畫畫就必定得筋骨,有分量;你畫畫好了,懂得氣韻生動,跡遇神化,你寫的字,刻的印還會死板僵硬嗎?誠然,有了結實的“一專”,才利于觸類旁通,一樣樣地去打通,才能抵達融會貫通、三絕一通。要之,急于求成講詩書印畫的全方位出擊,給人全能多才的表象,是沒有意義的花架子,是不可取的。
12開花與結果
老話說,春華秋實,其實學藝術到出成績,特別出大成績,卻不是有先后早晚之別,且是有著極大反差的。以繪畫為例,張大千二十多歲就畫得很好了,出名早,這樣的花可謂是春花,還有些三、四十歲出成果,這個年齡段是繁花似錦的開花大宗期,我稱這是夏花。有些六十多歲名望大了,如吳昌碩、齊白石,這是秋花。如果秋天不開花,冬天或許能開花,鍥而不舍,如黃賓虹就是典型的冬花,他八十歲之前還臨摹四王不大佳,他要到85歲之后才開始出彩,89歲到91歲左右我以為他畫得最好。故而花有早開與晚發之分。在座的都非常年輕,有志于篆刻藝術就要以終身的力心去探求,春花不開待夏開,夏花不開待秋開、秋花不開冬花開,如果在座的有的到了深冬,花還是不開,也是說一年四季都不能開花了,那么也不要泄氣。我們心平氣和地講,或豁達地想,稿藝術的剔除功利心,本諦是陶冶心靈、變化氣質,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,能在百花爭艷的藝壇里蕩漾,心曠神怡,怡然自得,如菖蒲、似翠竹,青且碧。即使什么花都不開,心花怒放那也好呀!
百世太平
今天就講到這里了,凌晨四時匆忙爬起來理了上述的十二條,準備匆忙,可能有些講的也欠妥,欠完整,希望大家多批評指教啊,謝謝大家。

復制成功
×

 瀏覽器自帶分享功能也很好用哦~
瀏覽器自帶分享功能也很好用哦~



 瀏覽器自帶分享功能也很好用哦~
瀏覽器自帶分享功能也很好用哦~